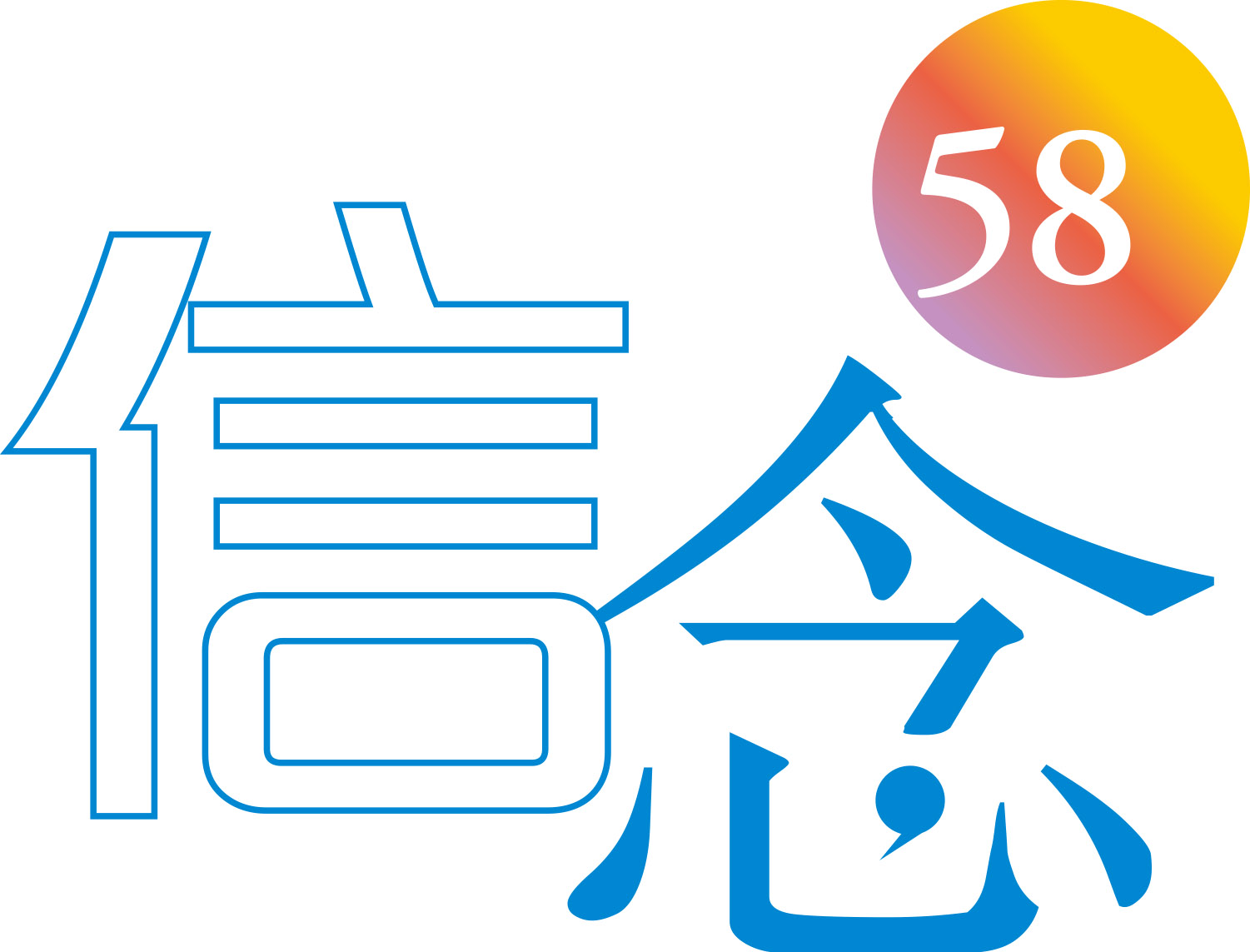Grad — 幕天席地剪髮的髮型師

05.2021 • Feature
採訪:Jonathan ╱撰文:周淑屏 ╱ 攝影:陳曉盈 ╱ 部分相片由受訪者提供
Grad在中學做暑期工時開始認識髮型師這行業,他當時覺得這份暑期工不錯,有音樂聽又可以涼冷氣。當時的心態是年青人甚麼都想嘗試,卻不算積極投入工作。九個月之後,師父問他有沒有興趣學剪髮,因為他之前只是做染髮、洗頭的工作,比較沈悶,於是抱着嘗試的心態開始學。學習之後,瞭解了頭髮的層次、結構,掌握到每個不同設計都有其線條上的特色,漸漸覺得很好玩,開始對剪髮有興趣。

無心插柳入行
他用了一年的時間學習,之後開始幫小朋友、中學生剪髮實習。師父鼓勵他去讀剪髮,因為剪髮時會有很多自己想不明白的地方,學校的老師會糾正剪髮的錯誤,對他會有很大幫助。後來,他在剪髮中有不明白的想找回這個師傅向他請教,但是那位師父已因為癌症離世了。Grad回想離開之前曾經看到他頭上的頭髮全剃光,原來那時已經是他人生的最後階段,對這位師父,Grad是既感激又惋惜的。
聽了師父的話,赴上海修讀剪髮課程後,他百分百肯定髮型線條的運用、操作,確定了自己要成為髮型師的路向。然而,在學校學剪髮之後,他發現學校教的剪髮技巧和商業應用有很大落差,曾經懷疑是否該堅持在學校學到的手法。他在1997年入行,2004–05年修讀剪髮,回來應用時,因為髮型屋都要求剪髮快、不太講究,令他感到很疑惑。幾經思考、掙扎後,他重新肯定在學校學到的,堅持用回自己的手法,不因為商業因素而改變。
不少髮型師都會粗製濫造,認為不需太執着,不需剪得太仔細。但他因為不認同這種得過得過且過的態度,所以和其他同行有點格格不入。對剪髮技術要求高的他,用心為客人剪完髮後,看到他們開心的笑容是由心而發的;有時客人在外面的髮型屋把頭髮剪到參差不齊,他幫他們把頭髮剪得整整齊齊,看見客人開心他就感到滿足。

開始上門剪髮
八年前,他去澳洲開始工作假期,那是因為他對香港業界粗製濫造的剪髮風氣沒有信心,想去外國見識學習。但是到了澳洲,卻感覺他們的髮型師剪髮技術沒有想像中那麼厲害。這期間,在澳洲的香港留學生找他幫他們剪髮,他便開始了上門剪髮服務。那些留學生住的屋下面有車房,車房裏有一塊全身鏡、一張凳,他就帶了裝有剪刀、風筒的背囊,和那些留學生一邊打邊爐一邊剪髮。因為那些留學生在外面找不到適合的髮型師,澳洲那邊的髮型師都會把他們的頭髮剪得很短,他們認為沒有型格,於是都找他幫忙,然後,一個介紹一個,他的客人也漸多。

Grad也由此對上門為客人剪髮產生興趣。他在剪髮時對燈光、光線很有要求,他會選有日光的時候剪,由於他要求高,髮型屋的工具不能滿足他,他寧願自己帶風筒、梳、剪刀、水壺、電鏟、大小鏡和凳,去客人的地方剪髮。有一次,他去客人家中剪髮,和那家人一家幾口在花園裡邊燒烤邊剪。他說:「我覺得這種形式的剪髮是與人分享,並非只是單純為別人服務。」在整個工作假期期間,最初他在髮型屋上班,最後的兩三個月他已轉為專門上門剪髮,這次的工作假期很愉快,令他留下了美好的回憶。
一張凳、一塊布
回港後,他很懷念在澳洲剪髮的那種感覺。在他離開香港時,很多熟客都希望他快點回來幫他們剪頭髮,一個客人曾經傳訊息給他,讓他看自己被其他髮型師剪得很差的髮型的相片。當這客人知道他已回港後,告訴他因為要去見工,急着找他剪髮。但是當時沒有適合的地方剪,客人就約他在火炭的一個公園中剪髮。在公園裏只需一張凳、一塊布,加上他自己帶去的工具,就可以幫客人剪髮。因為客人趕時間,要在晚上剪,而公園光線不夠,他們就轉了到行人隧道中剪。

最初Grad建議客人在戶外公園剪髮時,客人曾經猶疑,問他:「這可行嗎?」他反問客人:「你會不會和我一起瘋狂一下?如果在這裡剪髮被人趕走,我們就到另外的地方剪吧!沒甚麼大不了的。」之後,他和客人也對此次經驗感到愉快及有新鮮感。
剪髮到會服務
他時常和客人說在髮型屋中剪髮很悶,所以一些熟客也會約他在外面剪。他只會和相熟的客人在外面剪髮,熟客看到他在臉書上發放在公園中剪髮的照片,便跟他說:「不如到我家中剪髮吧!」由此他就開始了剪髮到會服務。剛開始時,他未有車,只是乘公共交通工具去目的地。雖然是在戶外剪髮,但是他也覺得需要提升對工具的要求,於是他買了一個畫架放鏡子,買了一張凳和小茶几。在戶外剪髮的安排很隨意,不會每星期也有約,今次在這裏剪,下次又會約在另一個地方,他認為這樣才好玩。

有一次到客人住的村屋剪髮, 因為客人家中的光線不足夠,他便建議到天台剪。那次的經驗很令人驚喜,因為剪髮時有麻鷹在他們的頭上翱翔。另一次,他和客人在上水梧桐河畔的草地剪髮,在戶外剪髮有鳥聲、流水聲,和在髮型屋中有嘈吵的音樂、客人談話,感受截然不同。在草地上為客人剪頭髮,讓他找回在澳洲時在藍天白雲下剪髮的感受。
放鬆、放下、放開
他常建議客人轉髮型、轉地方剪髮,他不喜歡死板,喜歡古靈精怪的點子。一次有客人請他在汀九橋邊的海旁剪髮,這是客人提議的,因為客人時常駕車或跑步經過,覺得那邊的風景很好。他們以為因為疫情大數人都不愛外出,那邊會沒有人,但去到的時候,看到有很多人一家大小在海旁休憩。小朋友初時以為他在畫畫,之後便好奇地觀看他剪髮,也有阿叔經過問他剪髮要多少錢,但他以沒有預約不會提供服務的理由婉拒了。

在戶外剪髮可以和客人開心交流,客人心情比較放鬆,什麼也可以說,不怕旁邊的客人聽到。在疫情下很多人也很抑鬱,在戶外剪髮的一至一個半小時中,他們可以坐下來放鬆一下,對情緒很有幫助。他作為聆聽者,覺得可以幫助客人紓緩壓力,更是一種心理輔導。他規定客人在剪髮時不可以用電話,不可以看雜誌,客人要安靜地坐着看着鏡中的自己一個多小時。在這段時間內,他可以和客人有較深入的交流,有一些說話客人不想跟朋友講,在剪髮時就可以沒有避忌,可以跟他談談工作和與家人相處,客人需要這種渠道去抒發內心。剪髮時他也會買來大家喜歡吃的東西,或者會邊飲咖啡、啤酒邊剪髮,享受剪髮的過程。
客人送古董車
現在他提供剪髮到會服務時,會將工具放在他的古董車上,這古董車原來有一個故事,這車是一位客人送給他的。他有時會嘗試不用金錢作為報酬去為人剪髮,起初,為這個客人剪髮後,這個客人會送他一些書或電子書作為報酬。後來,這個客人要移民,便請他接收自己的古董車。客人說不想隨便把這車賣給人,就叫他接受這架古董車作為剪髮的報酬。

他起初怕自己不懂照顧古董車,但自己那時沒有車,就抱着嘗試的心態接受。他曾經覺得這古董車很老土,但是那是別人的一番心意,只好接受。慢慢地他發覺自己把車停在路上有不少人注目,加上也不會和人撞款,漸漸覺得這車很有味道。這古董車是2000年出產的,是行政級座駕,真皮座位寬敞舒適,客人坐上他的車時會覺得座位很舒適,他也會跟其他客人講這位客人送古董車的故事。
不想得過且過
回顧自己的髮型師生涯,Grad覺得最大的障礙是怎樣和得過且過的人相處。他不喜歡在髮型屋中剪髮,因為覺得很侷促,而且髮型屋的老闆都只從商業的角度出發,追求客量多,剪得快,得過且過,所以每半年至九月他就會轉一間髮型屋再合作。
2020年初因為疫症開始,客人明顯減少,很多髮型同業差不多零工作,零收入,要節衣縮食度過難關。Grad覺得他們要找回初心,這個行業才會改變、才會有進步,才可以走下去。對於剪髮行業有些人抱着粗製濫造、得過且過的態度,他想到去制作其他工種的工作態度和經驗的短片,讓行家了解應該怎樣改善和進步。他會拍攝咖啡師、木工工作的影片分享,讓同業去思考和得到進步。起初有這個念頭是他剛從澳洲回港,發現澳洲有很多美髮業的髮型網頁,但香港沒有,於是在香港開展這些網頁,希望和行家密切交流。他也開了髮型師討論會的社交媒體專頁,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,希望令同業進步,令大家多點思考。